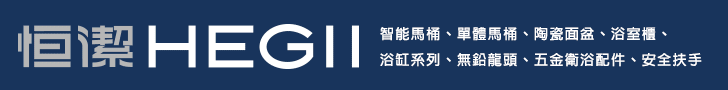專訪吳明益:面對暴雨將至 身為作家也要對抗

(德國之聲中文網)台灣作家吳明益在訪德期間的一場交流活動,與德國作家施益堅對談。提到台灣如今是中文世界裡唯一的民主國家,吳明益表示,台灣作為全世界中文出版最自由的國家,並非一朝一夕造成。過去他透過香港的出版社閱讀世界文學,如今台灣卻成了香港文化的飛地。
他表示,從文學角度來看,他很樂見包括中文、台文與原住民語寫作,皆歸於台灣這塊土地的文學成就,如此有利於台灣成為世界書寫文化的出版核心。
吳明益是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教授,目前班上12個人有1/4是香港人。他認為,近年香港很重要的一批年輕作家都來到台灣,日後雖可能不是台灣國籍,卻可能仍用中文寫作,只要他們在台灣的這塊土地上獲得尊重平等的對待,將成為台灣發聲很重要的一股力量。
DW:剛才提到研究所裡有香港學生,您觀察他們這群人身為學生或年輕創作者,心裡是不是非常動盪,有點不安?
吳明益:對,有些人帶著不安定感來到台灣。他們有些本來在香港就有成就了,不是到台灣才變成作家。其中20幾歲的居多,也有超過30歲的,香港雖然文學市場不是很大,可是他們有很多文學補助跟文學獎,像浸會大學也有創作學程,我個人覺得這一代香港年輕人,從事創作的蠻多的。
DW:因為命運的轉折,所以他們現在與原本關注的主題差很多?
吳明益:對,因為他們有些人參與過雨傘運動,或是家人有參與,自然會有一種緊張感,也會想把自己曾經經歷的時代描寫下來。
DW:剛才您說,這群香港創作者若獲得平等對待,會成為華文世界一股重要力量?
吳明益:是啊,因為台灣文學就是個混血的文學,有本土派的台文,像我讀書的年代,教科書都是中國古典作家,唸的是文言文,那些文學也確實影響了部分作家。又比方說我個人開始喜歡文學,是因為外國文學,我當時透過哥哥姊姊買的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庫來認識文學。當然後來我會回過頭去理解台灣文學,因為一方面認同,二方面其實你心裡也知道,必須對自己的立場找一個根基。
DW:什麼立場?
吳明益:以台灣文學的角度去看待世界的立場。比方說,我們現在都說我們台灣人、我們台灣文化,如果你也沒讀過什麼台灣文學、又是作家,怎麼樣都不合裡吧?總是要了解它的變動,理解過去作家的思考。
像我在寫《單車失竊記》,就是在寫這種文化的繼承。因為殖民的緣故,台灣很多美學或文化就是模仿日本人,他們就是向往日本明治維新後從西方獲得的一些東西。
小說裡為什麼寫腳踏車?因為當時台灣的設計都模仿日本的腳踏車,那是最modern的工具,但日本根本抄歐洲的啊,你可以找出一模一樣的美學痕跡。文學也是,那時風車詩社也是模仿法國的象徵主義,可是事實上很多人沒有去過法國呀,因為日本有一些作家是模仿法國的象徵主義,就形成了這種間接的模仿,從而自我實現。
我爸還在世的時候,我們不是富裕的家庭,但他只要正式出門,一定要穿皮鞋、戴帽子,所以他不是那種知識分子的台派,也不是平民的台派,他就是一個想要成為日本人的人,這樣的心態也真實地存在著。這些立場,都是從台灣的角度出發去理解的。
延伸閲讀——台灣: 華人閱讀世界的一扇窗
DW:現在有人提倡台灣人就是要學台文,老師怎麼看?
吳明益:我女兒小一,我看她的教科書同時有台羅音標,因為她們會有本土語文課,可以選客語、台語,那上面就用羅馬拼音,然後中文的部分用注音,然後還要學英文,所以她同時學了三種標音系統。可是看她也很自然,好像沒有覺得苦惱。
在我看來,台灣現在就是一個混血文化。或者說我更期待它變成一個混血的文化,不要有一個明確的、固定的定義,當然,這是我非常個人的想法。
DW:因為這樣比較自由?
吳明益:比方說一個創作者可以同時喜歡懂楚浮的電影,也可以欣賞泰國鬼片,覺得怎麼這麼離奇的方式表達,也可以看日本侘寂美學,長時間下來,說不定會產出一種前所未有的美學。
DW:剛剛對談老師有提到,寫作其實是一種療癒。寫作對於您,是一個怎麼樣的工具?
吳明益:橋樑,但這個橋樑不知道誰、什麼時候有人會走上來,你不知道。
我們用敏銳感去搭這種心靈橋樑,我也不知道目標,但你的敏銳覺得這好像有什麼,於是開始去建造它。
今年韓江得諾貝爾獎,她說她的作品在討論一件事:就是人性。作為一個作家,很重要的一個思考就是,人為什麼可以同時這麼高尚,又同時這麼卑劣?寫作的時候,作為一個作家,我總是斟酌要呈現哪一面。
DW:您寫作的時候會考慮到這個?
吳明益:我現在會啊,我年輕的時候可能就是模仿人家寫作,創作一定從模仿開始,然後慢慢有自主意識,你會有自己想追尋的東西,我想追尋的東西就是講我心裡的疑惑,各種的疑惑。疑惑不是真理,但是是追尋真理的開始。
DW:剛才提到現在創作時間變少,選擇創作主題會因此更謹慎?
吳明益:我學生常充滿熱情地跟我講他們想寫的題材。這很合理,20幾歲,創作的慾望就像熊熊烈火。
那我就會問:你真的愛這件事嗎?這件事真的在你的人生裡面起了一個很重大的心理作用嗎?或者你真的投入嗎?
比如說我小時候住中華商場,我寫《天橋上的魔術師》,我的同學被火車撞死了,那時候才8歲,你隔壁班的同學,你每天都看到他、跟他在天橋上玩,後來他被撞死,那真的是很詭異的一種情感,但是,寫這種情感的目的是什麼?
那時我們都還玩那個遊戲,就是火車要來趕快衝過去。
但是結果他死了,你以後對一個火車來衝過去這件事情,你會有一種很⋯⋯你也不知道是恐懼還是什麼,你一生一定會不斷回想那件事。它就變成我小時候的一個象徵,當一個重大事件迎面而來的時候,你也不再純潔了,你不再是那個衝過去不用怕的小孩。
我那一系列小說在寫這樣的一件事,因為我在中華商場那三千人一起住的,所以跟小家庭看到的人性是不同的。
DW:現在正在創作的小說?
吳明益:我現在正在畫一本繪本,寫完《海風酒店》之後,我讓裡面的角色長大,她變成一個繪本作家,把她跟巨人的故事畫出來,畫成一本繪本。
這本繪本其實是童話也是神話,也是我寫小說的時候,我腦袋裡的畫面,它跟小說不一樣。
(拿出手機秀出畫好的部分)
這就是小說裡面其中的一個情節,那個小女孩走到這個巨人之心的下面,她跟狗站在這個巨大的大樹下面。
DW:這個是你一邊寫作,腦中浮現的畫面?
吳明益:對,這棵大樹在繪本裡面是紅檜的紋路。這本繪本既是我創作的一個副產品,也是我的一個追求,因為藝術有時候就像是我剛剛講的,會把自己逼到絕境,作為一個小說作者去畫一個繪本做什麼?台灣有那麼多專業的繪本畫家很厲害的啊,有可能會被人家嘲笑說:畫得那麼爛還要畫圖。
DW:你會擔心?
吳明益:會呀,但也想畫圖啊。這就回到我剛剛跟我學生說:你有沒有愛?那我有愛,所以我撐住我這個壓力,盡全力把它表現出來。
DW:你想把它畫出來的原因?
吳明益:就像年輕時好想把心底的意圖寫出來一樣。我不是畫科普繪本,台灣有很多很棒的科普繪本,我也不是童話的繪本作家,我是一個有意識投入環境運動一段時間的小說作者,所以,這樣的繪本或者圖畫故事書,說不定就會有它的價值。
DW:這是你自己的定位?
吳明益:對,如果小說裡面有個角色,他很擅長煮義大利麵,而現實中我也變成一個很好的義大利麵廚師,這不是很棒的事嗎?你的藝術帶你的生活前進。因為你從事的藝術回頭豐富你的生活了。
所以我小說寫到一個主角,還去畫繪本,我也愛畫圖,我不是完全沒有自信畫圖,我認為我畫圖的直覺在水準以上,那我再努力一點,我就問很多畫家、我去學,透過一兩年的時間,把它畫出來,那不就等於我小說裡面那個角色?
為了把在她腦海裡,那個大家都認為已經死掉,根本是荒謬不可能存在的巨人,只有我看過的巨人,把那個經歷畫出來,就成了我的藝術使命。
那個角色,我替她完成他的使命,因為沒有她啊,她是我的小說人物,那豈不是又豐富了我的人生?
DW:這樣虛虛實實很有趣。
吳明益:對啊,所以我決定畫。
但既然要畫,我也不希望人家覺得這是小說家畫的繪本,標準降低,我也希望喜歡繪本的人也會說,「哦,這本繪本蠻特別的耶!」我想到達的地方是詩意。詩意是文學的核心,所以與其說我在畫一本繪本,不如說這是我的文學的副產品。
DW:包括《海風酒店》、《複眼人》很多段落都很像詩。
吳明益:因為我有一種感受,好吧,水泥廠已經蓋了,可是我還在和平村,我還在海豐村開麵店,每天就看著那個海。我要每天鬱卒也很過不去,但也不可能歡欣鼓舞,就只好面對,就像看著海浪看著星辰。
不是說你不恨那個工廠。能怎麼樣?有一天你去放火燒了它嗎?想像小說裡面寫放火燒了他,但現實的結果是我去坐牢,那還能做什麼?我就投入另外一個對抗這個世界的工作,繼續搏鬥下去。
DW:跟你人生的態度一樣?
吳明益:對,寫作一方面創作,一方面作為我的人生,所以我要把我自己活的跟裡面的東西接近一點吧。
DW:其實還是你追求的理想的樣子?
吳明益:對,比如說我當然覺得應該轉型正義、應該批判白色恐怖我們這些時代有點良心有知識的,都能理解這是共同的追求,問題是採取什麼途徑?
DW:在寫作的時候,會期待希望台灣政府因此有什麼轉變?
吳明益:我沒有欸,我都是看到某一個角色、某一件事點燃了我,我在做功課時或許有什麼東西,導致心有所感,我就試著去寫它、發展它,我甚至有時候我不知道我感知了什麼。促成什麼不是我能掌握的。
DW:不用釐清就可以寫?
吳明益:對,像《海風酒店》裡面開卡拉OK的老闆娘真有其人,她跟我講她一點都沒有感情,對水泥廠沒感情,對反水泥也沒感情,對她當時而言,只有賺錢才能保護自己。這麼一來,認真呈現這樣一個人物,說不定無意間也表現了,當時像她這樣要撐起一個家庭的女性的痛苦與意志。
DW:會蠻期許自己,不論是小說家或是自己的人生裡可以把人性看得通透?
吳明益:是迷惘,不是通透。我對人性迷惘,然後我對自己也很迷惘,我為什麼會做這種事?我也很矛盾,我就是一個比較懦弱的、比較沒有對抗意識的,覺得生命很多元。我自己會自我質疑,在寫小說人物時,常常引發我自己的自我質疑:你自己也不是什麼高尚的人。
DW:一邊寫作一邊跟自己衝突?
吳明益:會啊,因為我們小時候就是市井之民,我不是書香世家嘛,所以我像《天橋》裡面寫的那些小孩,就做生意並且用點小聰明欺騙客人,而且騙得很自然,很理直氣壯,你才能活下來,你才有機會變成不一樣的人。
我這個月要在高雄講戰爭電影、戰爭漫畫,我很喜歡那部馬其頓的電影《暴雨將至》,我自己就覺得,看著暴雨將至,你也擋不了他,你就要準備被淋濕了。
今年中歐朗讀節在捷克跟斯洛伐克,邀請20幾個台灣作家,一場演講有聽眾問說:如果中國真的攻打台灣,文學家能做什麼?我說,我怎麼辦?我想辦法把家人送到安全的地方或安全的國家,然後我留下來打仗。
我如果逃走的話,那我就對不起這個國家過去對我的一些幫助,我在藝術這個行業也受到國家的很多幫助,我如果投降或什麼,總而言之,我也心不安,這就是面對暴雨時,我直覺的責任。或許在戰爭中死了或什麼,你就要做心理準備。你就是面對那個暴雨,你一定會淋濕,你不會有一把傘,也許你還會有一支筆,有些人什麼都沒有,身為作家,你有責任用筆去面對疑惑,面對暴雨。
© 2024年德國之聲版權聲明:本文所有內容受到著作權法保護,如無德國之聲特別授權,不得擅自使用。任何不當行為都將導致追償,並受到刑事追究。
作者: 黃文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