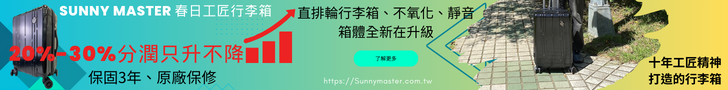客座評論:特朗普的外交策略——一朵「惡之花」?

(德國之聲中文網)在美國大選兩黨激烈對峙之際,一向關心國際事務的羅馬教宗方濟各曾敦促選民們“憑良心思考與選擇”,就墮胎及移民等敏感問題“兩害相權取其輕”。顯然,就大部分中間選民及觀察者而言,特朗普即使再度當選,亦有望於美國憲政框架之下節制其權力,更有機會汲取首次執政經驗的教訓與不足。
然而,縱觀特朗普繼任以來對幾大國際熱點的處理輪廓,卻令人質疑是否是一場史詩級的災難?短短一個月時間內,其為世界秩序所帶來的思想混亂與精神危機,似乎正在令人難以置信地想起法國詩人波德萊爾(Baudelaire)的《惡之花》(Les Fleurs du mal)。未來四年,美國的民主價值與民主形象將走向何方,委實成為一個需要不斷檢視的問號。
加沙地帶:家園情感 vs.“種族清洗”?
首先,針對巴以沖突,特朗普政府拋出的初步解決方案,顯然有悖國際法的道德准則:其雖提議美國接管並開發加沙,但卻一度建議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永久”遷出。這一方案即使看似能為加沙“地帶”帶來繁榮,但卻首先否定了巴勒斯坦人作為主體民族在此生活千年的生存權。
此種優先一切的“商業理性”(甚至有傳其家族將介入加沙房地產項目),摧毀的是巴勒斯坦民眾最原初的家園情感。縱觀歷史,即使加沙地帶曾落入奧斯曼帝國之手,但因流傳下來的古老地契,今日的土耳其手中仍有相關檔案庫及博物館等,能證實並承認巴勒斯坦民眾的房屋土地權。
更令人擔憂的是:特朗普政府還擬最快下月宣布“承認以色列對被佔領的約旦河西岸主權”。與之相對的是:在巴以戰爭爆發伊始,羅馬教宗方濟各便敏銳呼籲“耶路撒冷的所有神聖地點都務必維持現狀”——顯然:尤其是位於約旦河西岸的耶路撒冷為“三教聖地”(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為平復不乏血腥的歷史爭議,嚴格說來,其應一直依據聯合國《第181號決議》屬於獨立政治主體。
早在2017年,特朗普便在首任期間將美國大使館正式遷至耶路撒冷。這被外界解讀為對以色列實際控制耶路撒冷的默許,並激起了阿拉伯世界乃至包括東南亞穆斯林的不滿——此次哈馬斯發起的恐怖襲擊亦正是以耶路撒冷的清真聖寺阿克薩而命名(“阿克薩洪水”)。倘若此次特朗普在正式宣布以色列佔領主權之時,無法妥善處理巴勒斯坦視為首都的東耶路撒冷問題,恐會激起阿拉伯世界新的怨憤。
由此可見:特朗普政府的加沙計劃看似“高效”,卻引發了針對特定族群的“種族清洗”之嫌疑,亦被質疑是否撇棄國際社會長久以來、經由各種斡旋所達成的“兩國方案”。尤難想象的是:在激烈戰爭中遭受人道主義重創的加沙難民,不僅沒有得到任何喘息,卻即將面對流離失所的遷徙命運,顯然,這只會繼續強化巴勒斯坦民族的民族主義敘事。
俄烏戰爭: “帝國政治”與“殖民情結”?
有關加沙問題的巨大爭議尚未平息,聲稱24小時內停止俄烏戰爭的特朗普,呈現給世界的解決方案卻引起了“帝國政治”乃至“殖民主義”的質疑:在其提出的初步輪廓之中,美方本應作為世界道德秩序的代表,目前卻似乎過多地迎合普京的霸權主義;而面對實際受害者烏克蘭以及三年以來的利益攸關者歐盟一方,則較為缺乏基本的同理心與商榷意願。
首先:其不顧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歐盟與烏克蘭的呼籲,在隨後的利雅得美俄會談中直接排除了烏克蘭與歐盟。即使這僅是為了首先摸清俄羅斯的底線,但在面對來自於烏克蘭的情理之中的不滿,卻反駁暗示俄烏戰爭責任方甚至似在烏克蘭(“你們根本不應開始這場戰爭”、“你們本可達成協議”);並將烏克蘭的合法總統澤連斯基粗暴地稱為“沒有選舉的獨裁者”。
此種引發廣泛驚愕的運作程序與言談氣氛,令人情不自禁地想起充滿綏靖氣氛的1938年《慕尼黑協定》;並令人質疑特朗普是否已經公開淪為普京面對國際社會的傳聲筒?而特朗普政府目前關於烏克蘭所展現的“完美受害者”苛責(譬如萬斯副總統目前要求的烏克蘭“感恩說”),則似乎帶有某種“情感霸凌”色彩:即對受害者一方缺乏首要的同情,亦難以看到基於公義與道德支持的努力。
除此之外,爭議尤為巨大的是:倘若俄羅斯的領土要求沒有絲毫退讓,烏克蘭反而被迫單方放棄攻下的俄羅斯領土——這不僅將令烏克蘭在浴血奮戰之後沒有迎來任何“勝利”曙光,亦令歐盟與美國三年以來的巨額資金援助付諸東流。而倘若商人出身的特朗普亦心有不甘而最終獲得烏克蘭50%的關鍵性礦產資源(據稱等價約5000億美元),卻又並不真實提供任何具體性的安全保障,這或許難以平復公眾對其“趁火打劫”、“殖民情結”之質疑。
朝鮮半島及台灣:迷惘與“交易”?
如果說在上述錯綜復雜的俄烏戰爭、巴以戰爭之中,進攻方均聲稱自己遭受了某種程度的冒犯與挑釁,從而肆無忌憚地挑起了令沖突升級的野蠻武力,接下來令世人高度矚目的,則是特朗普將如何處理東北亞朝鮮半島的無核化問題以及台灣問題——畢竟,韓國與台灣均因歷史原因或國際公約,是面對核武或強權的“更弱小者”。
事實上,特朗普再度當選以來,韓國朝野已共同擔心:面對朝鮮核武可謂“手無寸鐵”、僅靠美軍薩德系統進行預警與防御的韓國,是否將面臨和烏克蘭一樣的“被邊緣化”命運(即被特朗普總統直接排除在朝美核談判之外)?由於韓國執政黨目前深陷尹錫悅總統彈劾案風波,一心接替執政的在野黨及黨首李在明,不惜改變一向的“反美”基調,急欲推舉特朗普獲取2025年諾貝爾和平獎。
而依特朗普急功近利、甚至不乏“慕強”色彩的“實用主義”原則,其已在繼職當日公開稱呼朝鮮為“核國家”(nuclear power)。但朝鮮曾因加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而本應背負無核化(CVID)義務,這打破了國際禁忌以及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六方會談”及國際原子能機構等的多年努力,無疑將進一步提高朝鮮的國際地位與談判籌碼,且很可能難以再實現朝鮮半島的完全無核化。而與此同時,被動的韓國與日本,則或許不得不從長遠角度提高軍備,甚至發展核武以自保。
而曾被特朗普喻為“筆尖大”的台灣,則更為擔心自己的安全利益失去保護。情急之中,意圖以更多的武器購買博取特朗普歡心並自保。但以台灣的體量與位置,即使尖端的軍事設備或亦無法完全保障其能有效抵御海峽對岸的多條戰線及人海戰術。而一旦台灣地區與韓國的地域政治博弈白熱化,其引以為傲的芯片開發或許難以逃脫以“保護”之名而徹底遷往美國本土的宿命——這樣一來,其將極大地失去在地緣博弈之中安身立命之競爭力。
結語
基於上述種種疑問,世界有必要對特朗普解決國際熱點問題的外交策略保持質疑與關注——畢竟,二戰以來,美國及美元所享有的全球“超級地位”,是因其捍衛了世界民主自由的基本價值及規則秩序。這不僅使其佔據了無可置疑的道德高地,亦為自己贏得了大批價值觀層面的長期盟友。
如果說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在就任美國總統初期,即敏銳地意識到了中國的崛起、世界格局的潛在改變,並尋求以貿易戰等挽回美國於全球化過程之中的衰落環節,尚屬情有可原、較為“有效”的國際動員;但其再任之後於國際自由民主秩序所造成的巨大震蕩,則著實令人迷惘。
在不久前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之上,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罕見地批評特朗普的世界觀“無視既定規則”,並一針見血地指出“民主不是一種商業模式”;而日前,針對烏克蘭問題紛爭,最新贏得聯邦大選的梅爾茲亦激烈批評美國已非“四十年前”其了解的美國,而且“大西洋兩岸之間的裂痕越來越深”。
或許,特朗普總統處理國際熱點的方式,稍有不慎,則有可能化作法國詩人波德萊爾筆下的“惡之花”:即因“和平”、利益等幻象之誘惑,甚至不惜打破禁忌,寄希望於“一日強似一日”的暗黑方式之上。而為了避免任何“惡之花”的綻放,國際社會有必要對“特朗普新政”保持種種警覺,以清醒而有效地達成協商與糾正、制衡與反駁之能力。
呂恆君(Dr. Hangkun Strian),華裔德籍漢學家,曾求學於韓國延世大學、檀國大學,並執教於韓國弘益大學、慶州大學等多所高校。此後在柏林洪堡大學亞非研究所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及興趣領域為文學史、電影、國際關系、基督宗教本土化等。
DW中文有Instagram!歡迎搜尋dw.chinese,看更多深入淺出的圖文與影音報道。
德國之聲致力於為您提供客觀中立的新聞報導,以及展現多種角度的評論分析。 文中評論及分析僅代表作者或專家個人立場。
© 2025年 德國之聲版權聲明:本文所有內容受到著作權法保護,如無德國之聲特別授權,不得擅自使用。任何不當行為都將導致追償,並受到刑事追究。
作者: 呂恆君